
门阀政治-东晋门阀政治:特权阶级的自我毁灭
日期:2024-01-13
来源:玫瑰财经网
浏览:次
(一)司马诸王的疯狂
我们评价西晋司马政权叫“生于不义,死于耻辱”。相比较于同样唱了一千多年白脸的曹操,司马家族是真正的“窃国者”。曹丞相不管怎样,北方的地盘都是他自己打来的,北拒匈奴,东征乌桓;开垦农田,兴修水利,恢复生产,军民同垦;唯才是举,提拔寒门。可以说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强大的曹魏政权:“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然而司马氏接盘了曹魏政权之后,虽然统一了中国,但马上就玩砸了。
三国两晋时期,正处在我国封建王朝由贵族地主阶级统治向士族地主阶级统治的过渡期,士族力量是一股蓬勃向上在很多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曹操死后,曹丕没有能力全面打压士族,同时为了代汉自立的政治野心向士族全面投降,颁布了“九品中正制”,曹操的“法家寒门路线”(陈寅恪语)可以说寿终正寝。然而士族阶级并不需要一个代理人,于是根正苗红的大士族司马家取代曹魏政权,也是注定之事。
然而司马氏成为皇帝之后,思维自然会发生变化,在野党和执政党的诉求肯定是不一样的。司马家族既然要“家天下”,自然不会与其他家族所共享。于是西晋统治者拍一拍他们聪明的脑瓜,想出来一个“天才”的策略:亲王统兵。后面的故事就不用我说了,八王之乱马上开打: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A被B杀了,C和D有联合起来杀了B,然后CD又开始内讧……最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西晋初年,司马诸王都要“就国”,就是回到自己的封国。他们一般都重视与封国内的士人结交(毕竟从本质上讲司马氏就是中国最大的士族),八王之乱中这些士族依附于司马氏,或怂恿,或合谋,兴风作浪。最终酿成永嘉之乱、五胡乱华的结局,司马氏是祸首,这些士族是帮凶。
“五胡乱华”的根本原因是司马氏把中原打空了,而直接原因则是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对峙时期,纷纷拉拢少数民族领袖作为外援,这二人,这二人是引胡骑入中原的直接祸首。最终八王之乱演变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导致五胡乱华。司马颖与匈奴人结盟,攻陷两京;而司马越则以鲜卑、乌桓为羽翼,南下进攻司马颖。可以看到“五胡乱华”的直接起因,是西晋统治阶级之间的内乱,并拉入了少数民族统势力以为羽翼,为少数民族南下提供了政治和战略上的契机。
石勒大家知道吧,“屠夫”的骂名背了一千多年。然而石勒最早是司马越之弟司马腾从并州掠卖于冀州的大量羯人之一,作为一个被掠夺、被买卖的奴隶,石勒对于司马越和司马腾的仇恨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这种仇恨很快就转化为了对整个汉民族的仇恨,永嘉元年,石勒起兵杀司马腾。然而无数的汉族百姓也被屠杀,当时民间流传的歌谣:“奴为将军何可羞,不分寒暑短人头”。可以看到,汉族贵族阶层对于少数民族平民的奴役、剥削与压迫是长时间存在的,而等到了少数民族平民“拉清单”之日,无数汉族平民相当于为统治阶级的愚蠢与贪婪买单。
当然,统治阶级的自我毁灭也受到了应有的苦果:“执太尉衍、襄阳王范、任城王济、武陵庄王澹、西河王喜、梁怀王禧、齐王超、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豫州刺史刘乔等。夜,使人排墙杀之。东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没。”——司马氏和士族阶级这些人全死在石勒的刀下,也算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
我们必须要看到,加入汉族统治阶级内乱的决策,也是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决定的,如匈奴刘渊等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逐鹿中原。然而最终买单的往往是双方的底层人民,种族仇杀。不得不说历史不忍卒读。
当然,在战乱下,包括司马氏在内的各大士族还是遭到了报应,用《晋书》里面的话说就是:“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然而罪魁祸首是谁呢我们都有答案。
(二)东晋门阀政治
司马氏把中原搞得一塌糊涂,也是自身实力大大受损,南渡避难之后,只能依靠士族的政治力量,宗室王公都要仰视于士族家族,“王与马,共天下”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五马渡江”的西晋诸王,除了元帝外,其余“四马”彭城、汝南、南顿、西阳诸王,都因不见容于士族权臣而丧生。正所谓“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司马氏的自我毁灭到此为止。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士族阶级的自我毁灭。
士族制度(包括九品中正制在内的一系列选拔制度)保证了士族拥有各种特权,他们世居高官,垄断朝政,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台湾学者毛汉光对两晋南北朝以上的文官4137人进行了统计,把他们分为士族、小姓、寒素三类进行过比较,他们之间为官的比例是7:2:1,士族任官占尽优势。西晋时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而到了东晋时期,士族为官比率高达90%以上。每一家士族都占有广大田庄山泽和附属于土地上的大量依附人口,这是他们赖以执政的经济实力。
《世说新语》说那些东晋时期的南渡士族“多名士,一时俊逸”,然而当代历史学家田余庆对他们的评价确是“这些人祖尚玄虚,多半没有政治能力”。我们读《世说新语》里面逸闻趣事的时候,可能会感慨:真是名士风流哈,说话做事就是出人意表。但是你要跳出这个思维的框框,再看那些“名士”的所说所作,你估计会去想:这人该不会是个傻子吧没错,兄弟!要相信你自己,这就是一群傻子!一般门阀士族的“创业一代”人才比率较高,再往后传承,因为优渥的生活环境和固定的世袭职位,从小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士族们极具缺乏社会经验和生活经验,更不要说治国治军治民了。例如建康令王复性从小娇生惯养,没有见过马。第一次看见马跳跃嘶鸣时,被吓得魂飞魄散,对别人说:“这明明是老虎啊,怎么说是马呢”
东晋的士族政权,只是代表江左士族阶级的利益,并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这一点从“北伐”的事情上就能看出。许多人对东晋偏安小朝廷持肯定态度,多半是它对于羯胡政权的“高姿态”,然而就如我们上文中所说,是因为南渡士族多出自东海王司马越的幕府,而司马越家族就是买卖石勒的人,因此被羯胡吊打,东晋王朝对于羯胡政权的敌视态度也就是顺理成章了。要是非要赋予东晋政权的民族性,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与鲜卑结盟,这还是当时司马越、司马颖相争下的政治格局。可以说哪里有什么民族,全TM都是生意。
比如当年少数民族军队逼近长安,愍帝遣使至建康,希望江左能出兵北伐缓解关中的压力,结果被司马睿、王导拒绝,最后长安不守、愍帝被俘——别说忠于人民了,他们连自己的皇帝都不在乎。等到了祖逖北伐,门阀士族也是多方掣肘。祖逖,就是那位“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的大英雄,被门阀士族的走狗戴渊掣肘,又被“王与马,共天下”所指的琅琊王氏中二号人物王敦所妒,东晋王朝真正的主人王导也自然就不待见他,无论在政策方面还是后勤方面都不给祖逖以支持,史书中经常出现“军中乏食”“进退失据”的记载。最终祖逖郁郁不得志,忧愤而终。朱熹看得很明白:“元帝与王导元不曾有中原志……当时是,王导已不爱其如此(指祖逖北伐),使戴若思(戴渊在《晋书》中因避唐高祖李渊讳作戴若思)辈监其军,可见如何得事成!”
等到了后来,所有士族阶级的“北伐”,无一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而非祖国统一的、民族解放的动机。例如先后居建康上游的庾、桓两大家族,屡次倡议北伐,直接目的都是巩固上游分陕势力,用北伐的大旗汇拢兵权,徐图朝廷。如庾冀北伐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不顾百姓嗟怨”也不顾朝廷劝阻,结果进兵至襄阳而止。史家对此都评价说“意在巩固(自己的实力),而不在羯胡”。 而桓温则更加明显,先后北伐三次,每伐一次夺一些兵权,剪除几个异己,直到独掌朝纲,废立皇帝。
后世学者们看得非常明显,不是说北伐就是为了民族利益、反对北伐就一定是汉奸,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南宋学者王应麟说得好:“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王夫之也这样评价桓温北伐:“若温果有经略中原之志,固当自帅大师以镇洛,然后请迁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进图天下,夫谁信之!”
士族阶级的膨胀与倒行逆施,是其灭亡的前奏。我们下面来看士族是怎么自己把自己玩死的。
(三)士族阶级的自我毁灭
“士族专兵”是士族阶级建立自己统治的根基,而士族“有兵可专”,是因为北方源源不断的流民南来,成为士族武装力量的最大兵源。然而士族并没有能力直接领导军队——就如上文所说,门阀士族除了个别几个杰出的人物,几乎所有都是智障——因此必须要靠“流民帅”来实现对军队的管辖。流民帅就是北方人民南下时形成的军事集团的首领,大多都是苦农民、苦大兵出身,而士族阶级掌握着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正好满足了众多流民帅的诉求,二者相互利用,一定程度上为门阀士族专政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野心从未减退,但流民武装对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侵有着天然的刻骨仇恨,因此在防卫东晋政权的战斗中有着很高的积极性,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障了江南的稳定。
当来自北方的入侵压力小了之后,门阀士族们就开始了“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内斗。整个东晋历史就是乱成一锅粥:先是王敦两次造反;然后镇压王敦的苏峻又造反;在之后就是庾氏家族和王氏家族在江州的火拼;等到庾、王两家元气大伤之后,谯国桓氏又异军突起,掌控中枢,废立皇帝;再到后来太原王氏家族内部后党和妃党左右互搏自相残杀……每一次门阀士族之间的斗争,都要大兴刑狱,当一方得势,另一方士族往往要面临屠戮之灾。至于波及、冤死者更不计其数。
直到前秦统一北方,苻坚率兵南下,来自少数民族的威胁又一次严峻起来的时候,士族阶级才稍微出来一个稍微有点人样的家族——陈郡谢氏。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战例,经常被拿来和赤壁之战相提并论:“一炬曹瞒仅脱身,谢郎棋畔定苻秦”“谁似东山老,谈笑静胡沙”——这里的“谢郎”“东山老”指的就是谢家领袖谢安。淝水之战的胜利就是靠谢安在中枢的运筹帷幄和谢玄率领将士们在前线的奋勇拼杀。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谢玄依靠北方流民和流民帅组建了大名鼎鼎的“北府军”,从此北方流民军事力量正式登上了东晋政治舞台。
然而谢氏家族以少胜多击退苻坚之后,随即又被“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东晋统治阶级夺权(谢氏家族理论上也算东晋的统治阶级,这次只不过是东晋无数次内斗的延续)。司马家族势力的孝武帝和司马道子随机夺了谢氏的权,淝水之战两年之后谢安离开中枢相位,赋居闲职;淝水之战三年之后,谢玄交出北府兵权。当轴门阀士族,不经过任何抵抗,在家族势力和声明如日中天的时候如此和平地让出中枢权力和军权,这不但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绝无仅有的,纵观中国历史也极为少见。为毛同为门阀士族的谢家这么老实,你堂堂皇帝和司马道子怎么就不敢拿桓温桓冲开刀,让人家骑在头上拉屎拉尿还是因为谢家觉悟高,识大体、知进退,《晋书》给予了谢安非常高度的评价:“不凭威挟主,不以外戚苟进,不借强枝压干”“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
然而整个两晋南朝,靠谱的士族恐怕只此一家。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夺了谢安谢玄的权之后,马上兄弟阋墙,自己开始内斗,史称“主相之争”。这二位的老婆也不闲着,她们分别属于门阀士族太原王氏的两枝,于是分别拉着自己的兄弟子侄们加入“主相之争”,分别被称作为“后党”和“妃党”,反正就是一群MDZZ的人又乱成一锅粥了。
统治阶级的内乱,使他们无法掌控一支重要的力量——北府军。当时士族武装大多腐朽不堪,由北方流民组成的北府军怀抱着恢复家园的理想,信念坚定、训练刻苦,又久经战阵,在与少数民族的频繁战斗中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成为了当时东晋唯一一支能拿得出手的军事力量。谢玄之后,各方势力虽然对北府军大力争夺,但是并无杰出人物能够控制北府军。北府将领,次等士族刘牢之(看着名字,王羲之王献之刘牢之,什么什么之,都是士族的标志,寒门是没有取这种名字的“特权”的)在一定时间内掌握了北府军的指挥权,然而刘牢之毕竟还带有着士族劣根性,依旧将依附于门阀士族作为自己的既定策略。于是刘牢之鼠首几端,一叛王恭而降司马道子,二叛司马道子而降桓玄,三叛桓玄最终走向绝路。
无论是门阀士族还是次等士族,都自己把自己玩死了,于是真正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真正代表北府军自身利益的“天选之子”出现了——刘裕。刘裕是正儿八经的穷苦出身:“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比较一下“寄奴”和“X之”这种名字,就能看出来阶级差异了。刘裕家境贫苦,母亲在分娩时去世,父亲一度想抛弃他。刘裕童年就开始砍柴、种地、打渔和卖草鞋补贴家用,有时为赚钱而去赌博樗蒲。刘裕就是从北府军里一点一点靠军功走上来的,比起那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族老爷,那可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最终刘裕也终成一番功业,推翻东晋,建立刘宋王朝,成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同时他数次北伐,恢复了北方大量领土,收淮北、平南燕、灭后秦——“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当然,门阀士族们自然是瞧不起刘裕这个苦大兵的。别说刘裕了,就连后起士族谢安也被那群装X装习惯的货色瞧不起:陈留阮氏嘲笑陈郡谢氏“新出门户,笃而无礼”(《世说新语·简傲》)。你瞧不起谢安,人家境界高也就算了,无非就是拯救一下你们这群废物然后归隐田园了;但是你瞧不起人苦大兵,那苦大兵还不教你做人东晋南朝的历史中,你会看到无数次这样的剧情:苦大兵们取得战功(一般是对战少数民族或镇压农民起义)——士族傲慢无礼,在精神上嘲笑苦大兵、在社会地位上歧视苦大兵,在政治上不满足苦大兵进步的愿望——苦大兵一看这个阶级天花板无法打破,忍无可忍起兵造反,锤爆士族阶级的狗头。于是南朝的历史总是在“有军权的寒门杰出人物建立朝代——士族阶级垄断做官权,抵制改革,与寒门皇权对抗——寒门杰出人物过世后,士族继续搞乱国家——新的有军权的寒门杰出人物建立朝代”这样的剧情中往复循环。
东晋南朝的士族们跟明末的文官士大夫们很像,都是属于养狗还不肯喂骨头的主。非但不喂骨头,还要羞辱狗,鄙视狗,对狗进行精神压迫。按理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军事实力,有枪有刀的苦大兵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但这就是一种天然的阶级自觉性和优越感,就像《大护法》里面的卯卯,就把花生人当做人和猪的区别,而门阀士族把小士族看成次等人,把寒门、苦大兵、老百姓就看成猪:什么猪也要做官也要跟我们平起平坐还有没有王法了
路琼之是宋孝武帝刘骏的亲戚(史书中有表弟或表侄两种说法),而王僧达是资深士族。因为做了邻居,路琼之去王僧达家拜访,但王僧达爱理不理,并且话里话外取笑他祖上是给自家喂马的。最严重的是,在他走之后,王僧之“焚琼之所坐床”。路琼之告到路太后,也就是孝武帝的妈妈那里,太后大怒,向皇帝哭说,“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后乞食矣。”孝武帝说,琼之年纪轻不懂事,没事去王僧达家干吗,不是自取其辱吗
侯景,也是一位历史著名的“苦大兵”,东魏叛将。投降南朝之后像求婚于士族家庭,屡遭拒绝和羞辱。后来侯景造反,攻入建康,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又向之前拒绝过他的士族们求婚,结果又是全遭拒绝。而且拒绝理由不是什么侯景终究要玩完我不趟这个浑水,而就是“门第不配”。你说吧,刀都架在头上了还这样,也不能指望他们什么了。
士族阶级取代贵族阶级,是有其历史进步性的;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士族阶级的统治又会落后于历史的潮流,最终被历史淘汰,这是大自然的辩证法。贵族政治多重血缘和继承,因此整个家族的发展受限于后代的成材率。然而士族的统治扩大了统治阶级的选择,不但会从血缘考虑,也包括了“门生故吏”这一特殊的阶层,比如我们上文中提到的戴渊,就来自于司马越琅琊王氏的幕府,最终用来牵制祖逖。统治阶级的扩大有利于人才的选拔,而当权士族中,选择杰出人物掌握家族权柄,对于其门户统治地位至关重要。所以当轴士族在选定其门户继承人时,往往是兼重人才而不专重嫡嗣,宁重长弟而不特重诸子。在东晋之初,士族子弟还可以胜任武职,出守边郡,当时的士族还尚有一些活力。
但是,士族阶级毕竟存在其固有的局限性,人才的选拔相较贵族政治虽然有所扩大,但还远远无法满足统治一个国家的需求。两晋南北朝的士族虽然重视人才,但是经过三代、四代之后,士族的腐朽程度普遍增加,人才越来越匮乏;士族阶级往往会选择在极小范围内通婚,因此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生理学上的退化。然而三代、四代之后的士族家族凭借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依然能够担任重要的官职、军职,这也是两晋南北朝大范围动乱的根源所在。等到侯景之乱的时候,士大夫们一个个都细皮嫩肉骨骼柔弱,连路都走不了,他们体弱气虚,受不了天气冷暖变化,因为这样猝死的,比比皆是——这大抵可以算作是“自我毁灭”的典型特征了。直到科举制建立起的庶族地主阶级的统治,才真正的满足了封建王朝的统治需求,延续了千年之久。
毫无疑问,士族搞乱了中国,但受到最大伤害的永远是中国人民。先不说在五胡乱华中惨遭屠戮的底层人民,单是在南朝短暂历史中,就平均一年就会爆发2.1次局部或全面战争,这是门阀士族争权夺利带来的最大恶果。像“苦发乐属,枉滥者众,驱逐徙拨,死叛殆尽”类似的记载遍布史书。读两晋南北朝历史,最能体会到什么是鲁迅先生笔下“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阶级社会中历史的进步,本来就是以人民的苦难为代价来取得的。
唐由之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眼科专家,一次他为毛泽东上门检查时,发现毛正捧着一本书老泪纵横,无声自泣。唐由之赶紧上前劝慰:“主席,你不能哭,千万不能哭,眼睛要坏的!”毛才慢慢平静。唐去看那本书,发现打开的那也是南宋词人陈亮的一首《念奴娇·登多景楼》,毛指其中一句良久不语,词曰: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相关文章阅读
-

500吨汽车吊作业性能表(汽车吊支腿反力及抗倾覆验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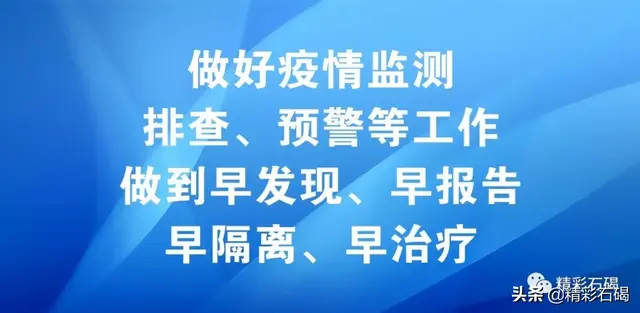
石碣镇汽车站(今天,石碣汽车客运站恢复运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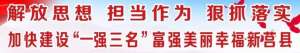
招贤汽车站(9月14日起,莒县K601路增开大站快车)
-

北京福田汽车图片(自重不到两吨,详解福田领航S1小卡)
-

东风轻型汽车(“东风轻型车”横空出世 未来无人驾驶车将快递送到家门口)
-

周口市汽车东站(郑阜高速铁路上的主要客运站——周口东站)
- · 汽车划痕修复技术(掌握汽车刮痕修复技巧,为自己攒下小金库)
- · 汽车换球头价格多少(球头坏了汽车什么症状)
- · 中国汽车关税(100%关税,中国电动汽车刺激了谁)
- · 汽车设计公司(涨姿势|国内有哪些好的汽车设计公司)
- · 济南汽车总站北区电话(济南长途汽车总站所有班车已“应停尽停”,出行请打96369)
- · 霸锐汽车优惠(10T的思域能买吗40万买霸锐还是途昂|答读者问)
- · 北碚区汽车站(重庆北碚的水土老街,曾是江北县城的所在地,如今却破败不堪)
- · 邹平到青岛汽车时刻表(今日起,恢复运行)
- · 汽车按键图标大全(一图看懂汽车内所有按键)
- · 太原建南汽车站地址(太原建南汽车站复工,已开通阳泉、平定等方向的8条线路)
- · 汽车尿素加盟(车用尿素设备多少钱一台)
- · 玩具汽车的图(男人真正大玩具牧马人JL25寸升高,上37寸轮胎真过瘾)
- · 汽车原厂脚垫(那些中看不中用的车内脚垫该扔就扔,还不赶紧看看你的车是不是)
- · 微信汽车游戏(2023年最受欢迎的微信大屏抽奖互动游戏有哪些怎么免费制作的)
- · 汽车机械钥匙怎么配(汽车钥匙全丢了怎么办如何配汽车钥匙,要准备什么资料)
热点推荐
最新新闻
Copyright (c) 2022 玫瑰财经网 版权所有
备案号:冀ICP备17019481号
玫瑰财经网发布此信息的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玫瑰财经网不保证该信息(包含但不限于文字、视频、音频、数据及图表)全部或者部分内容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及时性、原创性等。
相关信息并未经过本网站证实,不对您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