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啤酒吧侍者-《双脑人》入院(四、-五)
日期:2024-01-13
来源:玫瑰财经网
浏览:次
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
双脑人
[美]迈克尔.克赖顿 著
孙宗鲁 阿榛译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
入院 1971年3月9日(星期二)
四
“我还是不明白。”公共关系负责人说。
埃利斯长叹一声。但麦克弗森却耐心地微笑着。“这是一种能引起暴力行为的器质性疾病,”他说道,“你就这么看好了。”
三个人坐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饭店里提前吃晚餐。这是麦克弗森出的主意。麦克弗森要埃利斯来,因此埃利斯就来了。
埃利斯举手招呼侍者再来点咖啡,想使自己保持清醒。反正他今晚不会睡多少觉,更不能在对人体做这种手术的前夜睡什么好觉。
他知道在上床以后也会辗转反侧,翻来覆去地琢磨他早已熟悉的手术步骤。他已在许多猴子身上做过这种手术,准确地说,154只猴子。猴子很不好对付。它们拽去缝线,拉掉电线,尖声吼叫,跟你撕扯,张口乱咬。
“来杯白兰地?”麦克弗森问道。
“好。”公共关系负责人说。
麦克弗森用眼睛凝视埃利斯,意思是问他要不要。埃利斯摇了摇头。他在咖啡里掺了乳脂,往后坐了坐,抑制住了一声呵欠。说真的,这位公共关系负责人与猴子有几分相像,像一只十几岁的罗猴:一模一样的短而粗的下颚,一模一样的机灵劲儿。
这位公共关系负责人名叫拉尔夫。埃利斯不知道他姓什么。搞公共关系的人从来不讲他的姓。当然他在医院里并不被人称作公共关系负责人。他是医院的情报科长或新闻科长或是什么别的该死的东西。
他确实像只猴子。埃利斯发觉自己老盯着他耳朵后面的颅骨。这正是该植入电极的地方。
“我们对那暴力行为的原因还知道得不多,”麦克弗森说,“社会学家提出的学说挺多,反正是纳税人付钱呗。但我们知道有一种病,就是精神运动性癫痫,确实可以引起暴力行为。”
“精神运动性癫痫。”拉尔夫复述道。
“对。这种癫痫就跟其他癫痫一样普遍。有些名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得过这种病。我们研究所认为,这种病可能极为普遍。那种反复地搞暴力行为的人,像有些警察、匪徒、暴徒、所谓‘地狱天使’,很可能就有这种病。但谁也不曾想过这些人实际上有病。一般都以为世上有不少脾气暴躁的人,这是正常现象。也许情况并非如此。”
“我明白了。”拉尔夫说。他确实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样子。埃利斯想:麦克弗森恐怕当过小学教员,他的天才在于教学,他从来没有搞过多少科研。
“所以,”麦克弗森用手梳了梳自己的白发,说,“我们还说不上精神运动性癫痫到底普遍到什么程度。但我们猜想大概有百分之一至二的人可能受到这种病的折磨。这就有200万到400万美国人哩。”
“啊呀,天哪!”拉尔夫惊叹道。
“由于某种原因,”麦克弗森一面说,一面朝端来啤酒的侍者点头示意,“精神运动性癫痫在发作时容易引起暴力或过火的行为。其中原因我们不清楚,但这是事实。此外,还伴有性欲亢进和病态性酗酒的现象。”
拉尔夫突然显出很有兴趣的样子。
埃利斯想到他那第一位要做第三阶段手术的病人本森,身材短粗的小个子本森。这位仪表温和的计算机程序编制人员,在酗酒后把在场的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毒打了。在脑子里穿上电线!用这种办法来治愈那种怪病似乎有些荒谬。
拉尔夫好像也这么想。“手术能把暴力行为治好吗?”
“是的,”麦克弗森说,“我们坚信能够做到。但这种手术过去从来没有在人体上做过。明天早晨将是第一例。”
“我明白了。”拉尔夫说,似乎突然明白了麦克弗森请他吃饭的原因。
“从报纸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题材。”麦克弗森说。
“噢,是的,我明白………”拉尔夫的话头停了停,又问道,“那么,由谁来开刀呢?”
“就是我。”埃利斯说。
“喔,”拉尔夫说,“我得查一查卷宗,看看有没有你最近的照片,还得为新闻发布准备一份精采的小传。”他想到自己马上要做的不少工作,不由得皱起眉头。
埃利斯为这个人反应感到惊奇。他所想的全是这些么?要照片干什么?但麦克弗森却若无其事。他说:“你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
这次会面到此结束了。
———————————————
五
罗伯特.莫里斯正在医院自助食堂吃一块不太新鲜的苹果排,身上的呼叫机突然尖叫起来,持续不停。他伸手关掉了别在腰带上的呼叫机。但没等他把最后几口吃完,呼叫机又尖叫起来。他咒骂了一声,放下餐叉,赶去打电话回答那呼叫。
当初他刚用上别在腰上的这个小灰盒时,他还觉得这玩意儿很新鲜。他常常津津有味地想起自己同一位姑娘共餐时突然听到这呼叫机呼叫的情形,这表明自己是一位十分忙碌、身负患者生死重任的人。每逢这一情况出现时,他便会立即请求姑娘原谅他要走开一会儿,然后去打电话,焕发出一种责任感。姑娘们都爱这一手。
几年过去,这玩意儿就不新鲜了。这盒子毫无人性,而且绝不宽容。对他来说,这盒子已标志着“身不由己”。他永远成了一个当班的、被人任意使唤的人,而且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可能找他。也许是一位护士在半夜两点钟找他询问白天的医嘱中有什么问题;也许是一位家属在他母亲手术后的治疗上找麻烦;也许是通知他赶紧去开会,而他早已坐在会议室里,正开着那该死的会哩。
如今,他最美妙的时刻是回到家把那盒子一扔数小时不管。这时他才自由自在,谁也找不着他啦。
他一面拨着电话,一面瞅着远处那块未吃完的苹果排。
“喂,我是莫里斯大夫。”
“莫里斯大夫,请打2471。”
“谢谢。”
这是七护士站的分机号。奇怪,他怎么记得这些分机号码的呢!附属医院的电话网络简直比人体解剖还要复杂。但一年年过去,他用不着故意去记忆它,就全都记住了。他打电话给七楼。
“我是莫里斯大夫。”
“噢,是的,”一个女性的嗓音回答说,“有一个女人给本森送来一个短途旅行包,说全是私人用品。您说可以给他吗?
“我来一下吧。”
“谢谢您,大夫。”
他回到餐桌旁,端起托盘,送到餐具和剩饭处理的地方。这时,他那呼叫机又叫了起来。他又去打电话。
“我是莫里斯大夫。”
“莫里斯大夫,请打1357。”
这是新陈代谢室的分机。他又拨了电话。
“我是莫里斯大夫。”
“我是汉莱大夫。”一个嗓音不熟悉的人回答道,“你能不能来看一看一位女病人。她患的是溶血性贫血,准备做脾切除。我们认为她现在可能有类固醇性精神病。”
“今天看不了啦,”莫里斯说,“明天的时间也很紧。”后面一句话,简直是轻描淡写,因为今年的工作实在忙得要命。“你找过彼得斯吗?”。
“还没有。”
“彼得斯对类固醇性心理障碍很有经验。找一找他吧。”
“好吧,谢谢。”
莫里斯挂断电话,走进电梯,按了去七楼的按钮。这时他那呼叫机第三次叫了起来。他看看手表。下午6时30分。这时他应该算是下班了。但他还是去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凯尔苏,小儿科住院医师。
“你的屁股想挨揍啊?”凯尔苏说。
“行啊,什么时候去打球呢?”
“嗯,半小时以后,好吗?”
“只要你弄到网球。”
“我早弄到啦,就在我车里。”
“那就在网球场见面,”莫里斯说,又加了一句,“我也许稍为晚一点到。”
“别太晚了,”凯尔苏说,“天快黑了。”
莫里斯说他会尽快来的,便挂断了电话。
七楼很肃静。其他楼层都在这时刻挤满了家属和探视的人,十分喧闹,但七楼永远是一片静谧。这是护士们悉心维持至今的。
护士站的护士说:“她就在那儿,大夫。”说着朝长椅上的一位姑娘把头一扬。莫里斯朝她走去。她很年轻,非常俊俏,服饰华丽,好像是娱乐性行业中的人,两腿十分修长。
“我是莫里斯大夫。”
“我是安吉拉.布莱克,”她站起身来,很拘谨地同莫里斯握手致意,“我给哈利送来这个,她提起一只小小的蓝色短途旅行包,“是他叫我送来的。
“行啊,”他接过旅行包,“我会转交给他。”
她踌躇了一会儿说道:“我能见见他吗?”
“我想不太合适。”此刻本森应该剃过头了。做了剃头等术前准备的患者常常是不愿会客的。
“只要几分钟时间。”
“他已经吃了不少安眠药了。”
她显然很失望。“那么,可不可以请你捎一个口信给他?”
“当然可以。”
“请告诉他,我回我的老公寓了。他会明白的。”
“好吧。”
“你不会忘记吧?”
“不会,我一定转告。”
“谢谢你了。”她嫣然一笑。尽管浓妆艳抹,还装着长长的假睫毛,但这一笑却很动人。年轻姑娘为什么在脸上搞那些玩意儿呢?
“我想我该走了。”她动身离去,短裙下的长腿迈着轻盈而坚定的步伐。他瞅着她离去,然后掂了掂旅行包。它沉甸甸的。
坐在710室门外的警官问了句:“挺好吗?”
“挺好。”莫里斯应了一声。
莫里斯把旅行包拿进屋子时,那警官盯着这个小包,但什么也没有说。
哈利.本森正在看电视。一部西部片。
莫里斯把音量捻小。“这是一位很漂亮的姑娘给你送来的。”
“是安吉拉吧?”本森微笑道,“对了,她外表好看。内部机制并不复杂,但外表好看。”他伸手接过小包。“她全带来啦?”
莫里斯盯着本森打开小包,把里面的东西放在床上。一套睡衣、一把电剃刀、一些剃须后用的香液、一本平装小说。
本森又取出一个黑色的假发。
“这是什么?”莫里斯问。
本森耸耸肩。“我早晚得用它。”他大笑起来,“你或迟或早总会让我出院的,是不是?”
莫里斯跟他一起大笑。本森把假发扔进小包,又拿出一个塑料盒来。咔嗒一声,他将它打开,原来是一套型号不同的旋凿。
“这是干什么用的?”莫里斯问道。
本森似乎有难言之隐,一会儿才说:“我不知道你能否理解……”
“唔?”
“我总是随身带着它,为了保护。”
本森把它放回旅行包,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几乎近于虔诚的神色了。莫里斯知道病人常把一些古怪的东西带进医院来,病重时尤其如此,把它们当作图腾似的,好像具有护身的魔力。而这些东西往往同癖好或心爱的活动有关。他想起以前有一位患转移性脑瘤的快艇驾驶员带来一只修理船帆的工具箱,还有一位患严重心脏病的妇女随身带着一筒网球。如此等等。
“我能理解。”莫里斯说。
本森微笑了。
相关文章阅读
-

500吨汽车吊作业性能表(汽车吊支腿反力及抗倾覆验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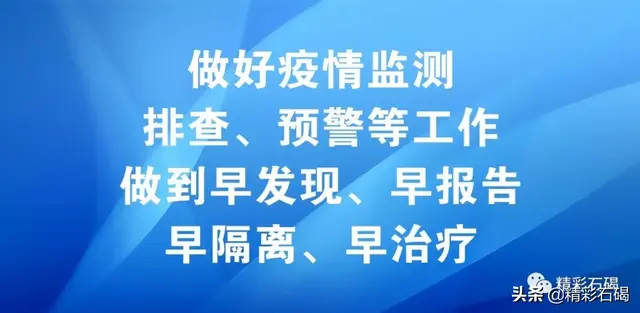
石碣镇汽车站(今天,石碣汽车客运站恢复运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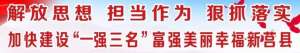
招贤汽车站(9月14日起,莒县K601路增开大站快车)
-

北京福田汽车图片(自重不到两吨,详解福田领航S1小卡)
-

东风轻型汽车(“东风轻型车”横空出世 未来无人驾驶车将快递送到家门口)
-

周口市汽车东站(郑阜高速铁路上的主要客运站——周口东站)
- · 汽车划痕修复技术(掌握汽车刮痕修复技巧,为自己攒下小金库)
- · 汽车换球头价格多少(球头坏了汽车什么症状)
- · 中国汽车关税(100%关税,中国电动汽车刺激了谁)
- · 汽车设计公司(涨姿势|国内有哪些好的汽车设计公司)
- · 济南汽车总站北区电话(济南长途汽车总站所有班车已“应停尽停”,出行请打96369)
- · 霸锐汽车优惠(10T的思域能买吗40万买霸锐还是途昂|答读者问)
- · 北碚区汽车站(重庆北碚的水土老街,曾是江北县城的所在地,如今却破败不堪)
- · 邹平到青岛汽车时刻表(今日起,恢复运行)
- · 汽车按键图标大全(一图看懂汽车内所有按键)
- · 太原建南汽车站地址(太原建南汽车站复工,已开通阳泉、平定等方向的8条线路)
- · 汽车尿素加盟(车用尿素设备多少钱一台)
- · 玩具汽车的图(男人真正大玩具牧马人JL25寸升高,上37寸轮胎真过瘾)
- · 汽车原厂脚垫(那些中看不中用的车内脚垫该扔就扔,还不赶紧看看你的车是不是)
- · 微信汽车游戏(2023年最受欢迎的微信大屏抽奖互动游戏有哪些怎么免费制作的)
- · 汽车机械钥匙怎么配(汽车钥匙全丢了怎么办如何配汽车钥匙,要准备什么资料)
热点推荐
最新新闻
Copyright (c) 2022 玫瑰财经网 版权所有
备案号:冀ICP备17019481号
玫瑰财经网发布此信息的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玫瑰财经网不保证该信息(包含但不限于文字、视频、音频、数据及图表)全部或者部分内容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及时性、原创性等。
相关信息并未经过本网站证实,不对您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